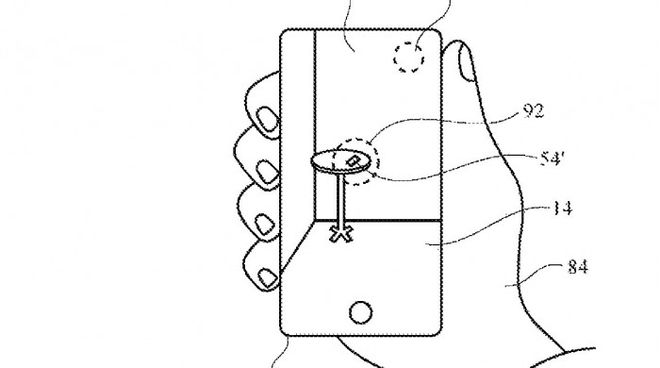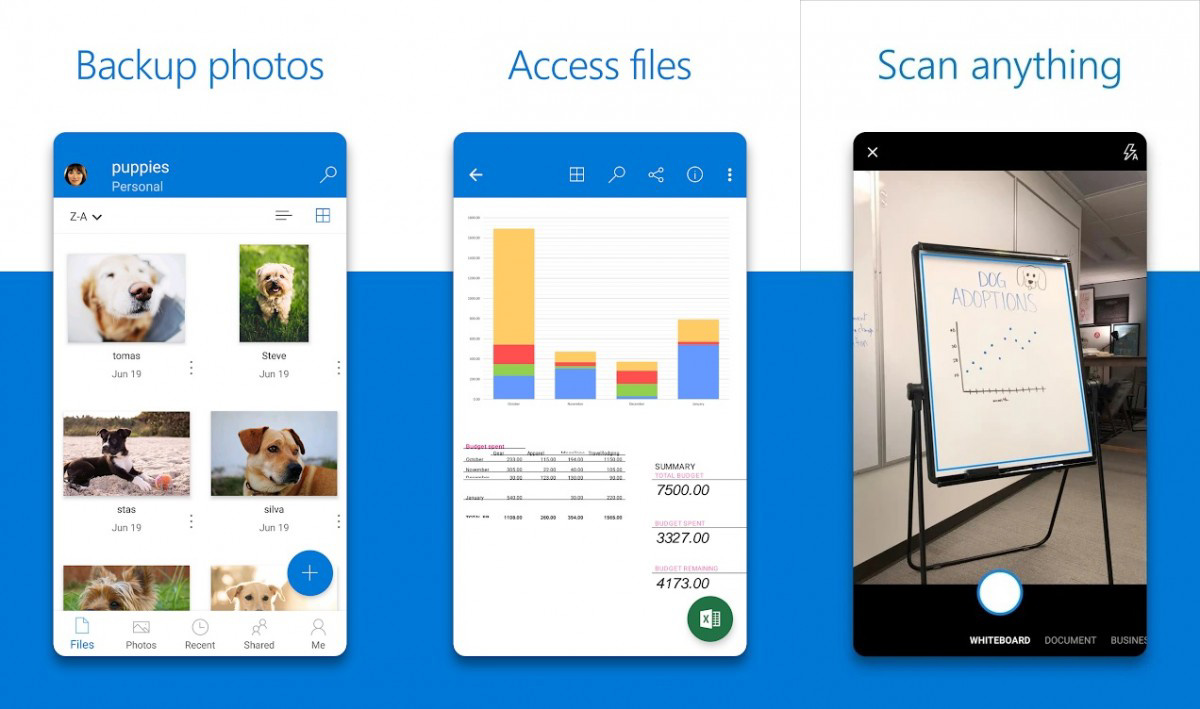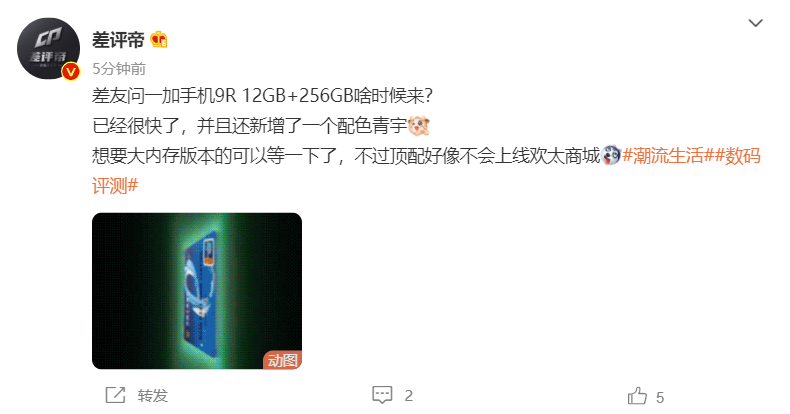虧損、倒閉、重生,LiveHouse逃離生死線
年輕人正在涌向LiveHouse,將這里作為精神烏托邦,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消費并沒能撐起這一行業。
近些年,LiveHouse成為年輕人喜愛的一種現場音樂場所,但作為舶來品,LiveHouse一直難以擺脫小眾的標簽。
前不久,成都小酒館迎來了25歲生日,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搖滾樂隊和獨立音樂人都在現場為小酒館慶生。
老狼來了,并唱了一首聲音玩具的《沒有人能夠比我們更接近對方》,聲音玩具的主唱歐迦源則翻唱了老狼的《虎口脫險》。在場的還有音樂人丁薇、李泉、木瑪、邊遠以及馬賽克樂隊、海龜先生樂隊、阿修羅樂隊等。
??老狼在成都小酒館 受訪者供圖
某種程度上,小酒館是國內元老級的LiveHouse。二十多年前,主理人史雷從北京來到成都,經營小酒館至今,一路見證成都獨立音樂走向蓬勃發展的同時,也伴隨眾多本土原創樂隊成長。
在國內,存活如此多年的LiveHouse并不多見,杭州酒球會同樣是少數之一。成立于2010年的酒球會,是杭州最老牌的LiveHouse。多年前,主理人王滌在北京河酒吧聽民謠,那是野孩子樂隊創辦的一個民謠音樂人“聚集地”,萬曉利、小河、張瑋瑋都算是那走出來的民謠歌手。
后來,河酒吧支撐不住而倒閉,王滌萌生了在杭州開一家LiveHouse的想法。于是,酒球會成為他心中河酒吧的另一種延續。不過,經營LiveHouse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酒球會也曾一度走向倒閉的邊緣。
??酒球會的演出現場 受訪者供圖
《2020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20年,音樂類演出票房總收入73.79億元。其中,Livehouse票房收入3.75億元,僅占到演出大盤5%。
2019年對LiveHouse是個契機,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將新褲子、痛仰、刺猬等獨立樂隊推向臺前,LiveHouse也迎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隨著熱度逐漸趨于冷靜,更多LiveHouse還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
越來越多的LiveHouse決心從“情懷”走向“生意,探尋生存之道,這不僅關乎是否盈利的現實意義,更為重要的是,走過探索階段的LiveHouse,下一步應如何面對行業不斷發展帶來的商業化難題。
01 夢想照進現實
對于大多數擁躉者而言, LiveHouse不僅是一處單純的演出空間,更像是一個“精神烏托邦”,一群人為了某種“歸屬感”相聚在此。
LiveHouse背后的主理人,多數也是源于這樣的初衷入行。
鄭州7LIVEHOUSE主理人沈毅曾在大學時期組建過樂隊,后來樂隊解散,他又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創業,2007年,他決心開一家LiveHouse。“回到這個行業做這個事兒,是自己的熱愛和夢想。”沈毅說。
??7LIVEHOUSE 受訪者供圖
夢想照進現實,現實卻極為殘酷。起初,包括他在內還有幾位合伙人,但開始運營后,人員卻不斷減少。“當時的合伙人都是音樂愛好者,也有原來樂隊的成員,大家本來就沒有什么經濟實力,更沒有想過經營LiveHouse會這么艱難。”
一開始,7LIVEHOUSE沒有任何模版和方向參照。“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做適合樂隊的演出場地,而且在十幾年前,不管是場地、設備,還是樂隊、市場環境都還不成熟。”沈毅坦言,7LIVEHOUSE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摸索階段。
“那段時間,一般的演出大概只能賣出去三、四十張票,甚至更少,房租都不夠付。”沈毅稱,成立至今,7LIVEHOUSE前后投入200余萬元,直到2017年才基本做到經營的收支平衡,后續逐漸盈利。
如今,7LIVEHOUSE依舊是鄭州唯一一家LiveHouse。在沈毅看來,“如果沒有真正的熱情支撐著,做不了這個生意。”
王滌有同樣的心境。2014年,王滌一手創辦的酒球會處在倒閉邊緣,當時距離開業已經過去4年。“最難的時候欠了接近600萬元,靠著向很多朋友借錢才能維持經營。”王滌直言,那是酒球會的一次“生死關”。
后來,經歷一些經營調整,酒球會的收益才逐漸穩定。但直到現在,也算不上真正賺到了錢。“酒球會每年的營收還在用來還之前的債,原本預計2020年將欠款都還清,但因為疫情影響,還款時間只能延后。”王滌說道。
02 在生死線徘徊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批國內老牌LiveHouse相繼關停,能存活至今的LiveHouse是幸運的。但某種程度上,幸運來源于痛定思痛后的改變。
情懷和經營,很長時間在LiveHouse主理人心中是兩個矛盾的存在。體現在現實中,多數LiveHouse長期都因為只講情懷而在生死線徘徊,直到他們開始將LiveHouse當作一門生意。
此前,LiveHouse基本依賴演出票房維持收益,而票房的好壞取決于樂隊自身流量和名氣。但樂隊成長本身又需要一定時間,某種意義上,LiveHouse成為樂隊的“培養皿”,承擔了一些演出風險,經營收入更難以穩定。
“到目前為止,真正做到靠演出能夠盈利的場地,全國不超過20個。”王滌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最初,他只把酒球會當成夢想,沒有從商業的角度,符合基本的商業邏輯去運營。
“租場地、養團隊、維護設備,這些成本都需要營收來支撐,至少要把房租和員工的生活費掙出來,但是一開始我們都沒有做到。”王滌坦言。
多名LiveHouse從業人士都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LiveHouse的經營成本高昂,幾年花掉上百萬元是業內常態。
與此同時,LiveHouse還面臨“內容稀缺”的痛點,在目前的國內音樂市場,樂隊依舊不成規模,難以支撐LiveHouse的內容需求。
“數量上,國內樂隊相比國外便有一定的差距,現實中,能讓LiveHouse掙錢的樂隊更是少之甚少。”在沈毅看來,有流量的樂隊不夠LiveHouse分配,大多數資源更是掌握在頭部場地手中,三、四線城市的LiveHouse基本沒有機會。
從可持續商業化的運作角度來說,LiveHouse存在的瓶頸還有:難以實現標準化。
一方面,LiveHouse尚未出現清晰的商業模式,每個場地的商業化運營階段不同,盈利的方式也不同;另一方面,不管是人才、文化還是內容、形態,幾乎都存在差異。
2017年,拿下數千萬元Pre-A輪融資的MAOLiveHouse,曾嘗試在全國進行連鎖化擴張,通過全資和合資的模式進行經營。
但沈毅認為:“各地的文化氛圍不一樣,LiveHouse對于每個城市而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制定統一的規則并不容易,每一家LiveHouse本身都很有個性,是非規范化的。”
“也許未來會有巨大的資本把很多LiveHouse都收入麾下,但獨立的場地依舊也會存在。”沈毅相信。
03 奔赴下一場
逐利的資本自然也是看到了LiveHouse仍有想象空間。
最明顯的契機是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的播出。“《樂隊的夏天》不僅對獨立音樂、搖滾樂的音樂文化有推動作用,對整個LiveHouse產業也有推動的作用。”史雷認為,很多年輕群體逐漸將在LiveHouse看一場演出,當成一個文化的休閑方式,“就像去看場電影,或是看脫口秀、話劇一樣。”
一個明顯的感覺是,想投錢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據王滌透露,2020年,一家國內頭部的共享充電企業曾找過他談合作,想加入酒球會。“他們設想LiveHouse可以像小酒吧海倫司那樣,迅速達到快速擴張。”
7LIVEHOUSE和小酒館也同樣遇到投資機構遞來的“橄欖枝”。但沈毅認為,在沒有看到清晰的商業路徑之前,7LIVEHOUSE并不會接受資本的進入,“這會影響我對這個事業的初衷。”
史雷則表示,與資本的談判是雙方標準走向一致的過程,如果沒有達到,小酒館選擇保持獨立的狀態。
與資本或多或少的接觸后,LiveHouse經營者們被直接或間接“教育”,開始思考關于運營、坪效、內容在內的商業化考量。
今年2月,近百家LiveHouse的主理人在合肥聯合舉辦了“首屆LiveHouse行業論壇”。大家自費參會,坐在一起,整整聊了三天——關于如何堅持下去,如何生存得更體面一些。
打造一個“復合型”空間場所被反復提起。
比如,增加附加值業務,LiveHouse可以提供酒水類消費;或者做成音樂餐吧,提供餐飲服務;也可以舉辦Party、脫口秀,增加適合年輕人的活動。總而言之,需要把空間利用起來。
??酒球會 受訪者供圖
“酒球會一直在做酒水類服務,基本將酒水消費與live消費做到較成功的結合。”在王滌看來,想要獲得商業回報,就要學會“彎腰”去做很多事情。沈毅也透露,7LIVEHOUSE嘗試在LiveHouse加入簡餐,還有關于樂隊周邊的零售服務。
多元的其他可能性,還包括走出LiveHouse本身的空間。
2018年,史雷在成都創建文創園區“院子文化創意園”,尋求與城市文化和獨立音樂場景產生更多的連接,進一步孵化和激活年輕群體。在史雷看來,單純做LiveHouse的競爭壓力較大,這是小酒館與城市深入連接的方式,他想以更多的方式生存。
不止是獨立空間的迭代,沈毅正在專注于內容廠牌,孵化與培養本地樂隊,為他們提供唱片錄制及出品、宣傳推廣等一系列服務;而王滌準備做一個大型的音樂節策劃,帶年輕樂隊到全國各個城市巡演,讓更多新樂隊能走出來。
“也許有一天,國內會有一個城市像代表戲劇的烏鎮一樣,是一個跟音樂相關的地方,成為一個‘音樂愛丁堡’。”王滌暢想道。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19號商研社”(ID:time_biz),作者:涂夢瑩,編輯:洪若琳 ,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