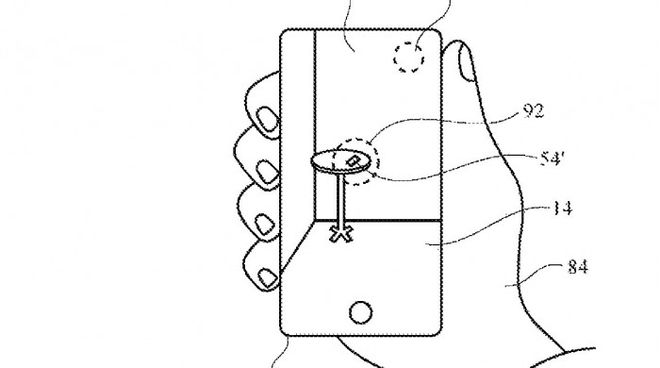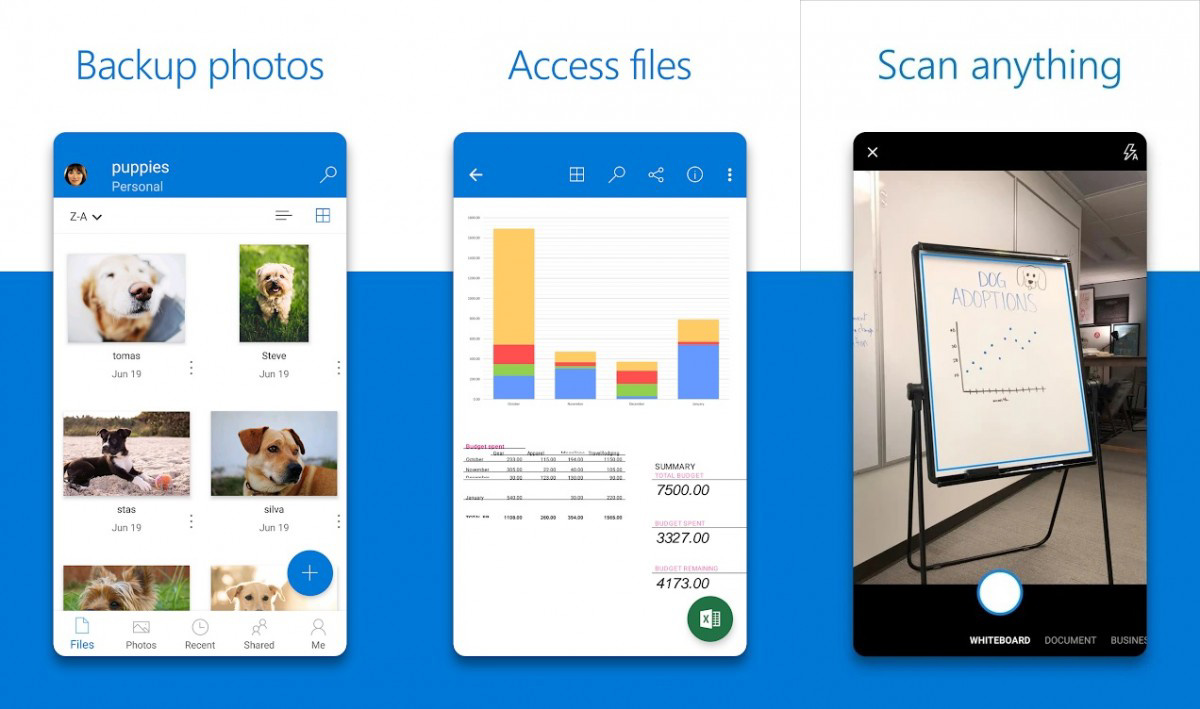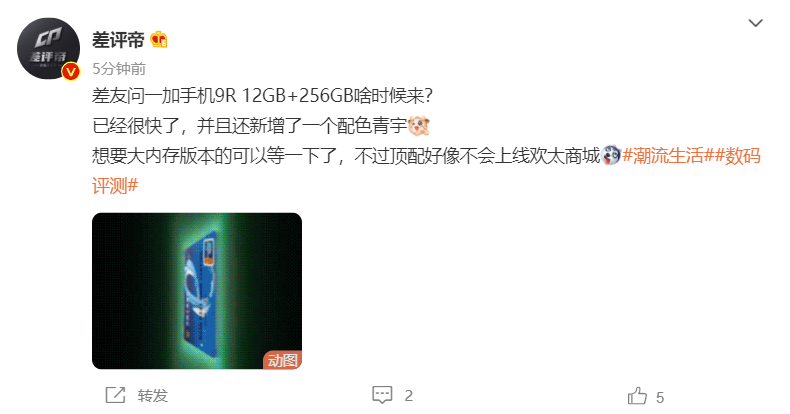昨日重現:算法改變了我們的懷舊
神譯局是36氪旗下編譯團隊,關注科技、商業、職場、生活等領域,重點介紹國外的新技術、新觀點、新風向。
編者按:未來屬于大數據,你能想到的一切正在被數據化,甚至包括文化藝術。研究表明,音樂正在變得越來越雷同。為什么?因為人們日益通過流媒體平臺收聽音樂,而這些普通會利用算法預測我們的品味并推薦歌曲。但這種根據過去預測未來的算法只會讓我們同質化,讓文化因為缺乏產生新想法、新可能性的資源而衰落。崇拜數字技術力量的那些人也許認為正朝著烏托邦邁進。但是,如果我們讓算法替我們所有人預測未來,我們就會發現,除了回到過去,我們別無他處可去。文章來自編譯。
圖片來源:Pixabay
劃重點:
音樂與消費者被簡化成數據
聽眾的口味會慢慢開始跟流媒體平臺所創建的模型類似
預測算法其實什么也預測不了,只能讓特定類型的過去重現而已
重新配置的文化藝術品看起來也許很新鮮,但其實卻是新瓶裝舊酒
推薦算法
2012 年,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人工智能研究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 Joan Serra 等科學家證實了一件很多人開始懷疑的事情:音樂正變得越來越雷同。這支團隊利用計算機分析,把近 50 萬首錄音歌曲按響度、音高和音色等變量進行分解,結果發現,自 1960 年代以來,流行音樂音色的多樣性就一直在減少。這種趨同性表明,流行音樂在朝著消費品的底層特征發展:遵循一種讓音樂得到病毒式傳播的公式。
這些發現標志著音樂發現行業走到了分水嶺。為了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歌曲的描述性元數據,從而讓算法可以推薦合適的歌曲給聽眾,這個行業已經付出了 10 億美元的努力。2010 年代初期,領先的音樂智能公司還是Echo Nest,然后 Spotify 在 2014 年收購了前者。 2005 年誕生于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Echo Nest 研究了一系列的算法,這些算法可以利用一組參數來測量錄制音樂,比方說原聲性(acousticness)、舞蹈性(danceability)、器樂性(instrumentalness)和言語性(speechiness)等名字比較拗口的參數。為了完善他們的模型,這些算法還可以到互聯網上面去搜索,并對描寫特定音樂的任何內容進行語義分析。其目標是設計出一首歌曲的完整指紋:把音樂簡化成數據,從而更好地引導消費者找到他們喜歡的歌曲。
最終,聽眾的口味就會慢慢開始跟流媒體平臺所創建的模型類似
到了 Spotify 收購下 Echo Nest 時,后者聲稱已利用一萬億個數據點分析了超過 3500 萬首歌曲。這些數據讓 Spotify 獲得強悍的推薦能力,可以跟蹤用戶的收聽習慣,并推薦相關的新音樂,把數據收集、分析與預測性干預集成到一個閉環之中。
科學哲學家 Catherine Stinson 是這樣描述這個閉環的:
事件序列是這樣的一個閉環,它從根據初始模型做出推薦開始,然后把推薦呈現給向用戶,并選擇其中部分推薦進行互動。這些互動會以標簽的形式提供顯式或隱式的反饋,用來更新初始模型。然后這個閉環會根據更新的模型提供新的推薦。
其結果是用戶會不斷遭遇類似的內容,因為算法不斷地推薦給他們。隨著這個反饋循環不斷繼續,慢慢已經沒有新信息可以添加進去;而算法的目的就是推薦出它認為肯定符合你品味的內容。
沒有哪個流媒體平臺可以準確預測品味;人類太善變了,沒法做出一致的預測。Spotify 的做法是建立用戶模型,然后通過推薦跟模型匹配的音樂來做出預測。一旦陷入到這些反饋循環里面之后,音樂風格就會開始趨同,因為過去推薦的依據是Echo Nest 描述器預先確定的詞匯。最終,聽眾可能就會慢慢接近流媒體平臺創建的模型。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人可能會變得對回聲以外的任何事物都無法容忍。
在 Echo Nest 的參數出現之前,20 世紀的音樂行業還要靠其他類型的數據去制作熱門歌曲。所謂的波普文化創造者(merchants of cool)會走上街頭去尋找下一個熱門趨勢,會對青少年的欲望進行研究,生成大量數據,然后用來輔助推銷下一個熱門話題。這種數據收集現在已經內置到收聽裝置本身了。一旦用戶用 Spotify 收聽了足夠多的音樂,讓后者建立起個人品味檔案(就變量的一致性而言,可以將其簡化為歌曲本身等數據),推薦系統就可以開始工作了。你使用 Spotify 的次數越多,Spotify 就越能確定你的興趣,或者做出預測的嘗試。(你準備好收聽更多的原聲音樂了嗎?)
將文化產品與消費者均拆解為數據,這不僅揭示了病毒式傳播的一個明顯的潛在公式,還促成了流媒體時代新型的公式化內容以及品味的渠限化(canalizing)。被簡化成零部件后,文化現在可以重新組合與優化,從而推動用戶的參與。這讓平臺能夠從積壓的內容當中榨取出更多的價值,并把預先存在的數據點重組為一系列新的相關性,推動新內容的創作朝著平臺最有能力處理,并能從中獲利的方向發展。(聽眾在 Spotify 上收聽針對 Spotify 優化的音樂受益最大。)但是,盡管這種重新配置的文化藝術品看起來也許很新鮮,但其實卻是新瓶裝舊酒。這有可能會導致文化因為缺乏產生新想法、新可能性的資源而衰落。
盡管這種重新配置的文化藝術品看起來也許很新鮮,但其實卻是新瓶裝舊酒
而在平臺環境以外的地方,社交互動往往是生成式(generative)的;想法靠分享或協作產生,大家的相互影響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進行。但在平臺之內,我們被歸類成數據,然后跟系統里面其他人的個人資料進行比較,這一過程叫做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作品是根據用戶的品味檔案以及消費過類似內容的其他人的檔案而做出的推薦。然后用戶以點擊作品的形式提供反饋,過濾算法則會對其推薦做出相應調整。這也許會擴大一個人的接觸面,但逃不出平臺的五指山,必須符合其計算預測的方向。平臺在你面前豎起的是一面鏡子,它不僅反映了你自己,也反映出你是怎么隨大流的。
如果你想凍結住文化,第一步就是把文化簡化為數據。如果你想維持僵化的現狀,根據人們過去的行為和品味訓練出來的算法將是最好的工具。就像凱茜·奧尼爾(Cathy O"Neil) 在 2017 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說那樣,他們在“重復我們過去的做法”。詹姆斯·布里德爾(James Bridle)解釋說,文化如果像算法一樣去思考的話,也會“投射出一個跟過去一樣的未來,因為當作數據收集的東西,建模的時候依據的就是它的本來面貌,然后向前投射——其隱含的假設是跟之前的經驗相比,事物不會發生根本上的改變或偏離。” 在一個依賴計算來理解事物的世界里,“探索可能性變成了探索可計算性”。
隨著將音樂拆解為計算機算法可以理解的參數的做法不斷深入,西方主流流行音樂的差異化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因為模擬時代的數據正在被重新注入到當下。很多新歌都是對舊歌的優化重排,試圖去利用算法分析檢測和實現出來的相關性。如果我們的口味稍有變化,算法就會做出調整,或者強行向我們提供它計算出來的,我們最有可能參與的內容,試圖逐步推動我們的口味符合它的設定。不管是哪種方式,推薦算法的目標都不是制造驚喜或震撼,而是確認。這個過程看起來很像預測,其實只是重復。結果是千篇一律:現在看起來像過去,而未來沒有未來。
復古誘餌
因此,懷舊不再只是對過去的“鄉愁”,在今天,有人還通過算法的干預,以改良的方式,主動去煽動這種情緒。這種新的懷舊不僅源自一個以數據形式呈現的世界;它還變成了不斷產生數據的誘餌。
剛開始的時候,平臺部分是靠外在的懷舊來吸引用戶:這也許可以叫做 “復古誘餌”(retrobait)。這種風格是 Instagram 在2010 年推出的。用了模擬攝影的那種氣氛和局限性來吸引用戶,Instagram早期的競爭對手 Hipstamatic 也這么做(新進入者 Dispo 現在也想這么做)。Instagram 推出了系列濾鏡,用戶可以用濾鏡在發布之前給自己的數字圖像增加一種模擬照片的朦朧感,從而把瞬間變成回憶。這種策略類似于給讓人回想起舊時流行文化的新作品嵌入的復活節彩蛋,比方說最近的電影《太空大灌籃》、《玩家一號》以及《無敵破壞王2:大鬧互聯網》(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等。
隨著社交媒體變得愈發的根深蒂固與無處不在,懷舊開始直接由平臺自身的性質塑造,就像 Timehop 一樣,這款app可挖掘過去的帖子,然后并向用戶展示他們過去發布過的內容,還有其他類似的算法性回憶功能,到了“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將內容重現。
在流媒體平臺這里,新舊內容是混合的,要進行再平衡,目的是要吸引和留住用戶,所以它們經常要求助于復古誘餌,誘騙用戶參與,以確保類似《辦公室》或《老友記》這樣令人垂涎的舊內容的權利。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制作了一些原創內容,就是把過去的一些節目元素進行重新組合(跟 Echo Nest 把歌曲分解成據稱可拆卸的核心組件很像)——算是一種精致的復古誘餌吧。
這種新的懷舊不僅源自一個以數據形式呈現的世界;它還變成了不斷產生數據的誘餌。
在 Netflix 上面,大家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比方說 《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說的是1980 年代一個虛構的小鎮里,一群小孩被迫與邪惡勢力作斗爭的系列劇;以及《紙牌屋》(House of Cards),這是Netflix 通過研究訂戶的品味特征而制作出來的原創劇。 同樣,迪士尼的流媒體平臺 Disney+,也通過《旺達幻視》(WandaVision)表達了對情景喜劇的懷舊之情,節目里面充滿了向《范戴克秀》(The Dick Van Dyke Show)、《布雷迪家庭》(The Brady Bunch)、《歡樂滿屋》(Full House)、《馬爾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以及《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等致敬的元素。當然了,還有無數的重啟、前傳或者續集。在音樂行業里面,復古誘餌趨勢往往表現為“流量作品(streambait)”或“Spotify熱門歌曲(Spotifycore)”,一種靠簡單公式創作出來的,充滿著對懷舊作品的借鑒,好方便算法推薦的音樂流派,用音樂評論家Jeremy Larson的話來說,這是“音樂當中最廉價的高潮”。
了解了平臺內置的激勵措施之后,通過制作自己的復古誘餌,獨立的社交媒體賬戶也可以擴大自己的知名度。你可以關注眾多的“懷舊美學”賬號,比如@publicschoolpizza、@rerunthe80s 以及@vintage.cheese等,這些賬號專門發布有關 20 世紀流行文化的內容,從 1980 年代的電視廣告到老式的軟色情都有介紹。有時候,這些賬號還會發布模仿過去風格的內容。Instagram 上面有幾十個“retrowave”或“synthwave”賬號,這些賬號會把舊的內容跟看起來很舊的新內容混搭在一起,對于像 General Mills 這樣希望讓復古營銷跟社交媒體協同起來的品牌來說,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做法。如果我在 Instagram 上滾動瀏覽那些復古誘餌賬號,app就會在我的Explore頁面展示來自復古誘餌賬號的帖子,然后這個反饋循環就會周而復始:因為懷舊進去,出來的也是懷舊。
對于希望從社交媒體的懷舊風獲利的投資公司來說,受到版權保護的舊內容非常有價值。Hipgnosis 與 Primary Wave 等基金會購買歌曲的版權,然后利用社交媒體推廣,再收取流媒體版稅。2020 年 9 月,佛利伍麥克合唱團(Fleetwood Mac) 的《夢》(Dreams)在 TikTok 上再度走紅之后,Stevie Nicks、Lindsey Buckingham 和 Mick Fleetwood 把歌曲版權賣給了一家專業基金,很快,TikTok 上面就出現了一波新的挑戰。
并不是說消費者一心只想要懷舊內容。但新奇往往會受到熟悉事物的限制:制作商會把包容性寫進重啟(比如 2016 年的《捉鬼敢死隊》),電影宇宙不斷擴張(從怪獸宇宙到漫威電影宇宙),舊規被廢除,換成了新規(如 2018 年的《月光光新慌慌》萬圣節重啟,對系列過去的所有電影追溯了連續性),并且越來越多過去小眾的微趨勢得以復興。這些姿態刷新了過去的IP,讓算法來放大,并為企業提供新的角度來推銷懷舊。
懷舊已經成為更多內容批量制作的模板,成為版權所有者新的收入來源,為平臺帶來新的數據流,讓用戶有了表明身份的新手段。有很多昔日的流行文化可供借鑒,平臺資本主義似乎永遠不會消失。他們告訴我們,收集數據是為了預測我們想要什么,但這并不完全正確。在嘗試預測我們的口味時,流媒體服務會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制作內容。由于算法是基于過去訓練出來的,所以就不只是通過中立的渠道把懷舊交給用戶;而且還在培養一種懷舊的偏見,試圖讓用戶更喜歡復古。
與此同時,科技巨頭技術卻大談未來,承諾用自己的技術提供沉浸式體驗和數字解決方案。但就算硅谷的自我定位是進步主義,但它的算法卻停留在過去。
昨日重現
預測算法并不能真正預測任何事情,那只是讓特定類型的過去反復出現而已。對歷史的特定理解(確認偏見或刻板印象)往往會被優先考慮,同時淡化或完全隱藏(非主流人群的)觀點。這往往是從媒體呈現中得到的歷史的可盈利的版本,而且由最大的媒體集團的 IP 主演:馬迪·麥克弗萊(Marty McFly)發明了搖滾樂;1960 年代只有《愛之夏》,沒有那場運動;得到五角大樓批準的漫威超級英雄;沒人死的汽車加速賽,哪怕是詹姆斯·迪恩也沒有(James Dean,因超速駕駛英年早逝)。
這種對過去的描述是準“官方”記錄,為特定目的服務,如粉飾大西洋奴隸貿易;歌頌哥倫布與羅伯特·李這樣的“偉人”的豐功偉績;或馬丁·路德·金的圣誕老人化。他們抹掉了的懷舊陰影,剩下的只有這樣一種懷舊:傳播對白人、規范以及消費主義的渴望,這跟巴迪亞·阿哈德-萊加迪(Badia Ahad-Legardy)所謂的“對懷舊的整體理解”是背道而馳的。
預測算法并不能真正預測任何事情,那只是讓特定類型的過去反復出現而已
過去的數據往往很暴力,很帝國主義——就像歷史學家西奧多拉·德賴爾(Theodora Dryer) 所說那樣,這是一種“殖民主義的數學”。這是歷史種族主義和偏執的數字。算法推薦想把這些數據轉化成懷舊情緒,轉化成不斷上演的將壓迫合理化的故事。但它利用的還是那些帶偏見的信息,讓貧富差距入籍,或者給刻板印象再注冊,因為已經太熟悉了還是詹姆斯·布里德爾(James Bridle)說得好,他是這么描述預測算法的,“因此,用先驗知識的殘余來訓練這些新生的智能,就是把……野蠻行為寫進我們的未來。”
算法決定論大規模地將人與事件鎖定進重復的循環之中,這是一個同質化過程,反映出社會本身被更大規模地同質化:獨特之處被夷為平地,變成無名之地,被媒體公司吞并。隨著元宇宙被大肆炒作,懷舊霸權的新時代即將到來。硅谷長期以來一直夢想著虛擬現實,而像 《玩家一號》 以及《黑鏡》第三季第四集《圣朱尼佩洛》(San Junipero)那樣的虛擬現實敘事,往往會承諾在假想中的數字天堂里面提供充滿懷舊感的自我實現——另一種形式新舊重組。在外面,社會正在崩潰,但虛擬宇宙為絕望的人們提供了逃避的機會:在受控的環境下,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化身,在我的世界(Minecraft World)里面閑逛,甚至可以跟蝙蝠俠一起攀登珠穆朗瑪峰。
盡管技術還沒有趕上這個夢想,但元宇宙已經被譽為可將知識產權摻和進來的數字領域。你可以是超級英雄,也可以是巨型機器人,你可以終此一生去尋找流行文化的復活節彩蛋。元宇宙有望成為我們的世界,就像所有關于虛擬現實所描繪的前景一樣,但它的前提和財源是析取出來的消費者數據,這些數據會被用來訓練算法,去推廣迪士尼和華納兄弟的知識產權,同時化解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努力。
如果把文化和消費者簡化成數據,只會繼續制造出同樣的懷舊表現,供保守的算法吐出推薦。崇拜數字技術力量的那些人也許相信,我們正朝著烏托邦邁進,以為人們可以逃離我們創造的未來。但是,如果我們讓算法替我們所有人預測未來,我們就會發現,除了回到過去,我們別無他處可去。
譯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