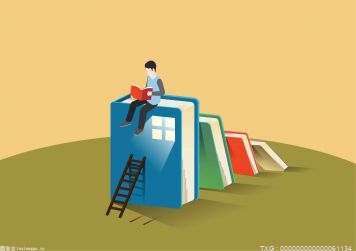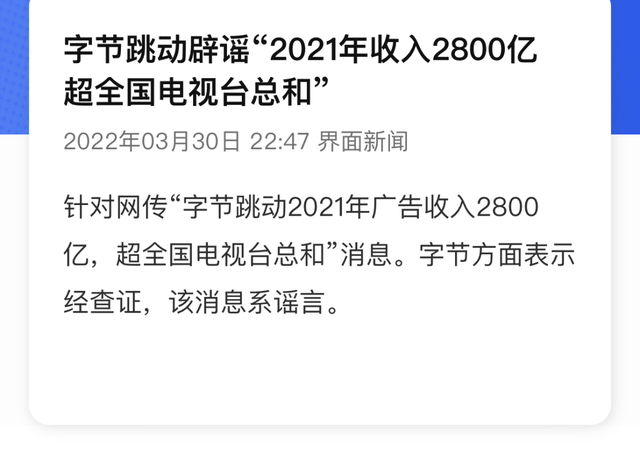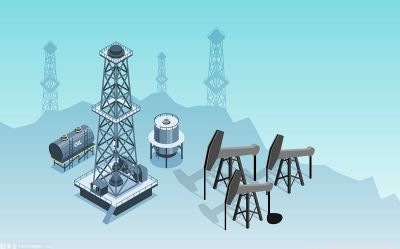森林野火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有多大?
地表可燃物的分解速率受地表溫度、濕度以及微生物作用的影響,也取決于可燃物自身的化學組成,木質素含量越多越難分解。所以低強度的火燒可以促進枯落物分解,適當增加土壤養分,如增加土壤鈣離子和鎂離子等陽性因子。
——劉曉東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
對林草和應急管理部門來說,每年春旱時節,森林防火成為重中之重。
“由于我國東北和西南有大面積的原始林,一旦用火失控,就可能導致大面積森林過火,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甚至威脅到人民生命財產和生態安全。山火所產生的大量煙霧,也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劉曉東告訴記者。
而在自然界,森林野火是導致生態系統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日前,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托馬斯·博爾奇團隊在《環境科學與技術》期刊在線發表一篇論文,對野火發生后土壤有機質中氮元素富集過程進行研究,與國內外其他研究相印證,重新引發了人們對森林野火弊與利以及生態修復問題的關注。
是否有益取決于強度和頻率等
森林野火是一種自然現象。“在陸地植物出現后不久,野火就出現在地理記錄中,它是導致生態系統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云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教授蘇文華說。
相關數據顯示,全世界年均發生森林火災20多萬次,燒毀森林面積占全世界森林總面積的1%以上。森林大火往往改變林木結構和森林環境,使森林生物量下降,生產力減弱,還影響了土壤的保水性、滲透性,引起沼澤化。
同時,森林野火也改變了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從而局部影響野生動物的物種多樣性及數量分布。如部分鳥類失去了棲息繁殖的樹木和可食用的果實,生存艱難;中小型哺乳動物失去喬木、灌木的庇護,暴露于荒野,無處躲藏。燃燒還會導致真菌菌絲死亡,可能降低森林有機質的降解速度。
但陸地生態系統也會經歷碳儲存與循環的過程。
“數億年來,野火影響著全球生態系統的格局和過程,影響著全球生物群落分布,并維持易受火災影響植物群落的結構和功能。火還可以作為一種進化過濾器,過濾易受火系統影響的某些植物特征。”蘇文華說,鑒于野火在生物領域中的特殊作用,長期以來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野火是一種類似于草食動物的標志性“消費者”。
“對森林生態系統而言,野火既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益的一面,這取決于火的強度、發生的頻率和面積大小。”劉曉東也認為,為避免更大的山火發生,國外一些國家會采取計劃火燒的方式來減少地表可燃物積累。
同時,一些研究表明,低強度的森林野火盡管在一定時期內對地表植被造成破壞,但對土壤理化性質有一定的改善,并形成空間異質性。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火燒跡地植被種類、數量會呈現上升趨勢,甚至會超過未過火林地,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重建森林樣貌需二三十年
植物光合作用不僅釋放氧氣,還造成枝葉等有機物堆積。在有雷電和不當用火等情況下,火災極易發生。
“為在易火生境中生存,大量陸生植物只有進化形成特殊的性狀,才能提高競爭能力。在火依賴生態系統中,森林野火并沒有顯著減少物種數量。”蘇文華介紹,云南松等眾多樹種就具有火依賴的生活史對策,它們需要一定時長的周期性過火才能維持其種群。“經過熱激處理,云南松和白楊等種子反而會有較高的萌發率。”他說。
云南松的松果成熟后不脫落,鱗片不裂開,內含種子的松果多年宿存在樹梢,針葉多年難分解。林火發生時,厚厚的鱗片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種子免受過高溫傷害。過火后,林冠上的松果鱗片綻開,釋放出種子。黑色種子落在黑色的余燼中不易被捕食者發現,經過雨季萌發并快速生長,使種群得以更新恢復。而且發生地面火時,云南松大樹基本不會受到影響,火后能繼續頑強生長,并補充新個體。
在蘇文華2015年從事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在距離超過200米的三個森林地塊上,山火發生后的156天,火跡地上有12棵喬木重新發芽、6棵高灌木和23棵一般灌木出現嫩芽,還冒出16種草本植物的新植株。除了幸存的松樹,所有被燒毀的喬木和灌木樹樁都有芽,重生率均為100%;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生物量分別為93.6%和73.9%。
“同樣,北方森林占世界森林分布面積的較大比重。火作為一個重要生態因子,在北方森林更新和碳循環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劉曉東說。
來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林學院的符曉2021年研究發現,在北方山火后第一年,雜草、苔蘚以及其他小型植物逐漸出現。從我國北方向西延伸到地中海,某些森林樹種適應了偶發的火災,例如多種松樹,大火融化了裹著種子的樹脂,方便種子傳播;又如栓皮櫟,大火中厚厚的樹皮起到了保護作用。火災后,一些存活下來的蒼蠅或甲蟲會被煙味吸引,因火災而變脆弱的樹木為它們提供食物和產卵地,而這些昆蟲又引來鳥類等捕食者。
記錄表明,山火發生2年后,新生的灌叢逐漸長出,先前逃離的狍子、野兔、山鶉、野豬等許多動物又重新回來定居;3到5年后,火災痕跡已不特別明顯,各類植物重新覆蓋土地,多種小灌木倔強生長;10年后,松樹可以長到3米高,苔蘚逐漸長成,多種動物逐漸回歸。20到30年后,先鋒樹種和本土樹種雜合,森林樣貌得以重現,其后大多數樹木將重新高達10至20米。
或改善森林土壤營養狀況
在新研究中,托馬斯·博爾奇教授團隊表示,“不同土壤燃燒強度下含氮土壤有機質和溶解有機質的富集,對生態系統恢復和土壤里的水質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認為,從不同燃燒溫度得出的分子組成表明,含氮副產物隨著加熱而富集。基于質量差異的分析還表明,加熱過程中形成的產物可以通過美拉德反應途徑的轉化來建模。森林野火極大地改變了儲存的和不穩定的土壤有機質、溶解有機質的輸出過程及路徑。
森林火災后的生態系統恢復,取決于土壤微生物群落和植被重建,而這些過程很容易受到土壤中營養物質的限制,如含氮物質和不穩定的水溶性化合物的多寡,都影響森林火災后生態系統的恢復。
蘇文華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過去人們更多認為山火會對有機物造成“很負面的影響”,但同時對不同野火強度下產生的土壤有機質及其副產物知之甚少,導致難以評估山火嚴重程度和預測生態系統恢復進程。“新的研究確實從新的視角解釋了人們過去一些不太清楚的方面。”蘇文華說,研究人員在野外看到山火對幼苗以及種子有“很促進”的生長過程,但人們對其機理不甚了了。新的實驗室研究從土壤微生物和分子的角度證明了機制存在的可能性。
劉曉東說,地表可燃物的分解速率受地表溫度、濕度以及微生物作用的影響,也取決于可燃物自身的化學組成,木質素含量越多越難分解。所以低強度的火燒可以促進枯落物分解,適當增加土壤養分,如增加土壤鈣離子和鎂離子等陽性因子。一些研究表明,在火燒跡地更新中,還有一個特征是豆科植物顯著增加。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具有一定固氮作用,這也是農事用火很普遍的原因。但由于南方很多區域林農犬牙鑲嵌,農事用火一旦控制不好,將導致森林火災的發生,因此,應加強對農事用火的監管和指導,做到疏堵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