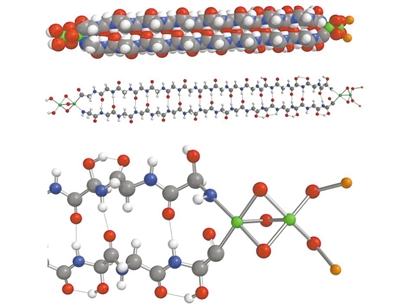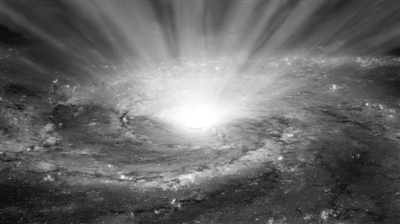清代宮廷防治天花的多樣“隔離法”,快來學習!

避暑山莊周乾攝
面對時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離的方法,即減少外出,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以切斷傳染病的傳播。我國古代中醫把傳染性疾病統稱為“瘟疫”,認為瘟疫發生時隔離病人,可控制傳染源,因而自古以來就有隔離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醫學典籍《黃帝內經》載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民眾如果得了傳染病,就需要被隔離到單獨的房屋里進行治療;《晉書》記載晉朝時若官員家里有傳染病人時,官員本人雖然沒有病,但百日內不允許進宮;《南朝齊會要·民政》記載,蕭齊時太子長懋等曾設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醫療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者;北宋醫學著作《太平圣惠方》記載當瘟疫進入百姓家庭時,需要開窗通風,這樣不會傳染等。
清朝是我國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時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瘡,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傳染性很強,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亂、傷寒一樣曾嚴重威脅著古人的健康與生命。當時的紫禁城里的統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離,即通過避痘、查痘、在熱河(承德)建造避暑山莊、設立圍班制度等方法,來達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離天花的主要方法。據清代史料筆記《北游錄》記載,1644年清入關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圍八十步都要用繩子圍起來,其他人不得入內。據史料《東華錄》記載,順治二年(1645)曾規定對天花患者進行隔離,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處各指定一村,作為京城里出痘者隔離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順治帝本人則采取停止大規模朝會或出宮暫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帝某次壽辰時,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賀禮;又如《北游錄》記載,順治十二年十一月,順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順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宮中每天去送碳的人,無論男女,只要沒出過痘的,都應該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剛出生時,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孫氏抱出紫禁城,進入北長街北口的福佑寺隔離。偏偏兩歲那年,他仍然沒有躲過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陰影仍時時籠罩在他的周圍。據清代官書《國朝宮史》記載,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宮中太監及宮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個月,尚在治療的須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進宮。避痘法雖然簡單,但效果良好。
為有效隔離天花,清代宮廷設立了查痘官員職位,即查痘章京。當時天花病人幾乎每年都有,宮廷規定的查痘的對象從八旗軍民擴及京城住民、出洋貿易者,以及來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發現癥狀,即進行隔離,要求患痘民眾遠離都城,或諭令未出痘外藩不能來京;對于隱瞞不報的,還將從嚴懲處。據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記載,查痘章京專職負責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檢查,凡是發現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遷移單獨的場所;在皇城外對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離性保護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圍內不允許天花病人進入;負責管理蒙古王公的進京事項,只有出過痘(得過天花且產生了抗體)的官員才能進京。
位于承德地區的避暑山莊(熱河行宮)是清代皇家園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卻是與隔離天花有關。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熱河巡查時,突然發現這里不僅是連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離天花病毒,自然氣候條件還適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宮,這就是避暑山莊的由來。清代皇帝每年5月來到山莊,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這里圍獵、召見群臣、批閱奏章、接見未出過痘的蒙、回、維等少數民族上層貴族及開展其他政治活動,駐蹕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熱河除了建造避暑山莊,還采取了相應的圍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領參與其主持的政治活動。所謂“圍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熱河舉行圍獵時,邊區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領分批覲見皇帝,并參與皇帝主持的圍獵、宴席等活動。
位于熱河的西北部的木蘭地區,面積近萬平方公里,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極好的狩獵之地。圍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補充形式。根據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進京覲見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稱為年班。期間,他們向皇帝獻上貢品,皇帝也會回賞禮物,設宴招待他們,舉辦各種歡慶活動,并了解各旗政務,以加強對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時,為避免天花傳染,皇帝下令凡是沒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來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熱河,九月隨皇帝木蘭圍獵,皇帝也可借此機會接見他們,并給與各種賞賜及娛樂性招待。此時熱河秋高氣爽,地廣人稀,可以較為有效地避免天花傳染。
限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條件,清代宮廷采取的上述隔離天花病毒的措施有著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對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開展各項活動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可以認為,上述隔離法是我國傳統中醫防疫理念的應用方式之一,亦能體現我國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