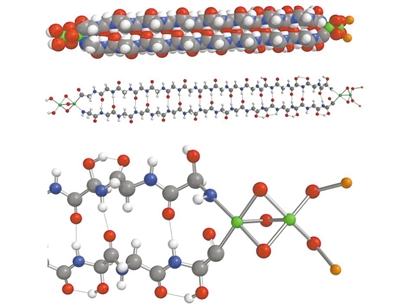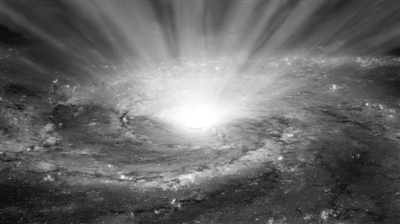"神藥"致癱:神經節苷脂注射液安全、療效再受拷問 賠償問題公司未回應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致電步長制藥證券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步長制藥神經節苷脂藥物說明書已經修改,并作出了相關提示,對于對患者賠償問題,目前公司還沒有相關信息。

圖/甘俊 攝
“已經花了40-50萬元,現在治不起,不治了。當時根本不知道‘神經節苷脂’類藥是干什么的,后來知道這藥很多病都有在用。”8月13日, 39歲的張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2018年4月他因車禍胳膊受傷住院,但沒有想到最終被確認為吉蘭-巴雷(格林-巴利)綜合征,至今癱瘓一年多,家里有三位老人兩個小孩要照顧,現在只有妻子一人支撐。
兩個月前張帆被人拉進一個80多人的吉蘭-巴雷患者群,這些患者接觸到這種病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為交通事故受輕傷,有的治療腦梗死,有的只是摔了一跤,但他們都在醫院被注射了“神經節苷脂”這類藥物,并在用藥后幾天之內癱瘓。
而這類藥物, 2016年11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發布了公告在說明書中增加警示語稱:“國內外藥品上市后監測中發現可能與使用神經節苷脂產品相關的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又稱吉蘭-巴雷綜合征)病例。”
這類用藥品種銷量超過數十億元,但是很多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對其不良反應并不知曉,相關生產企業亦未對該藥不良反應案例進行統計,至于全國目前有多少相關受害者也并不清晰。
但多位注射過“神經節苷脂”這類藥物的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為治療疾病都花費了巨額資金,在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記者采訪的相關患者中,他們治療費用平均在30萬元以上,有的甚至已經花費了100萬元以上,也有很多像張帆一樣因經濟原因放棄治療的。
王占群的妻子劉蕓也是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此前就醫期間亦注射了“神經節苷脂”等藥而導致癱瘓,至今已經花費30多萬元治療費用,就在他家附近還有好幾個因為這藥導致的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
當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問及是否有要求賠償的時候,王占群表示,還沒有去談,現在以治病救人為第一訴求。但他表示,現在國家正在整治“神藥”,希望這些藥徹底消失,不要傷害更多的家庭。
“神藥”被指為癱瘓誘因
2018年4月30日,因為交通事故胳膊受傷,張帆自己去了山西一家煤炭醫院,但在注射“神經節苷脂”5-6天后,腿和胳膊都感覺不舒服、沒勁,然后就從山西回到老家河北平山縣,在縣醫院住院一天,醫生又給他用了這個藥,病情加重,然后就到河北省二院住重癥監護室,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癥,但醫院還是給他用了這個藥一個星期。
“我在山西醫院花了2萬多元,然后在二院花了20多萬元,再回到平山縣醫院花了1萬多元,后在縣醫院看護費用又是十幾萬元,因為我是貧困戶,可以先看病再交錢,但現在治療了一年多,治不起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有妻子在做點小生意賺錢養家。”張帆無奈地說。
而僅在兩個月前,張帆才知道讓自己癱瘓、花費巨額醫藥費的吉蘭-巴雷綜合癥最大的誘因或是“神經節苷脂”注射所致,張帆也進了一個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群,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跟自己一樣注射了“神經節苷脂”類藥物,并且對該藥物致癱瘓的事情并不知曉。
而4月30日,王占群46歲的妻子劉蕓到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東院區做了甲狀腺切除手術,術后一切正常。5月9日,劉蕓基本康復,但到家后劉蕓四肢有些麻木,第二天四肢行動受限,5月11日凌晨竟然癱瘓了,后被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征,而經醫生等多方面推斷“神經節苷脂”系誘因。
2018年11月29日,69歲的章天君丈夫因腦梗死住院治療,其間相關病情癥狀得到控制,但最后被確認為吉蘭-巴雷綜合征,其間亦注射了“神經節苷脂”類藥物。
“跟我丈夫一起住院的也有好幾個癱瘓患者,我們互相交流,基本大致情況都是這樣發病。后來我們找到用藥說明書,副作用、發病癥狀等跟這些患者情況完全吻合。” 章天君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自己年紀較大照顧丈夫有點力不從心,包括治療、請護工等除了醫保報銷外總共花費超過30萬元。
讓張帆、劉蕓等癱瘓的吉蘭-巴雷綜合征是一種脊神經和周圍神經的脫髓鞘疾病,病情危重者會出現四肢完全性癱瘓,呼吸肌和吞咽肌麻痹,造成呼吸困難、吞咽障礙,生命受到威脅。
而他們都注射過的“神經節苷脂”,北京某三甲醫院神經科主任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說,該藥物治療腦卒中等急慢性腦血管疾病、老年性癡呆、顱腦外傷、脊髓損傷等原因引起的中樞神經損傷等,在臨床上神經科的醫生基本不用這個藥。這款藥既沒有有效的證據證明其療效,也沒有有效的證據證明其安全性。
早在上個世紀,神經節苷脂就被多國下架,一直被美國食藥監局(FDA)視為試驗性藥品。意大利學者Gianluca Landi也曾發表文章提醒,外源性神經節苷脂的使用與吉蘭-巴雷綜合征的發生密切相關。
而這個藥在2016年11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發布了公告在說明書中增加警示語稱:“國內外藥品上市后監測中發現可能與使用神經節苷脂產品相關的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又稱吉蘭-巴雷綜合征)病例。若患者在用藥期間(一般在用藥后5-10天內)出現持物不能、四肢無力、弛緩性癱瘓等癥狀,應立即就診。”
雖然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已經發布了對“神經節苷脂”類藥使用警示語,但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多位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中,他們表示此前并不知曉,而且他們所知道的其他患者甚至為他們治療的醫生也不知道國家已經對此類藥說明書進行了修改。
而且從銷量上看,此類藥物的銷售依舊是“火爆”。丁香園Insight數據庫顯示,神經節苷脂2018年的銷售額逼近40億元,同樣是一種含有神經節苷脂的藥物“腦苷肌肽”,2018年的銷售額亦達到22億元。
另據了解,為了加強合理用藥、有效控制醫藥費用不合理增長、降低藥占比,神經節苷脂已經進入多個省份重點藥品監控(輔助藥品)目錄。
國家版目錄第一批共列出20個西藥品種,集中在神經系統、免疫系統等領域。多個樣本醫院的數據庫統計顯示,這些藥在2018年的銷售額達到400億元至600億元的規模。
補償機制待健全
資料顯示,神經節苷脂類藥物涉及吉林步長制藥、齊魯制藥、吉林四環制藥、吉林英聯生物制藥、黑龍江哈爾濱醫大藥業等多家藥企。其中王占群妻子所用兩款神經節苷脂藥物,均由吉林步長制藥生產。當被問及是否有要求賠償的時候,王占群表示,還沒有去談,現在以治病救人為第一訴求。
就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致電步長制藥證券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步長制藥神經節苷脂藥物說明書已經修改,并作出了相關提示,對于對患者賠償問題,目前公司還沒有相關信息。
而另據了解,數家生產含有神經節苷脂藥物的生產企業,都沒有提供相關藥品上市后不良反應的監測信息。
北京亞歐雍文律師事務所醫療器械部主任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這種案例維權,法律上屬于藥品質量糾紛,分為兩類:藥品缺陷和藥品不良反應。可以適用產品質量法和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說明書如果已經明示了藥品的不良反應、適用范圍和禁忌癥等,對于廠家來說責任會減輕一些,但醫院也有一定責任,屬于醫療過錯責任追究范圍。
張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所在的患者群目前僅有四五個人進行維權獲得治療費用50%的賠償。“即便獲得賠償,對于一個家庭來說也是很大的打擊,而且醫生說這種病是終身受影響的,很多無法痊愈。”
浙江鑫目律師事務所律師章李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說,除了疫苗藥品,針對其他藥品,我國目前沒有針對“藥品不良反應”補償或賠償制度的專門立法。所以受害者需要根據侵權責任法、產品質量法等主張其權利。
但是由于藥品不良反應定義的前提是“合格產品”,所以藥品不良反應受害者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內難以從藥品生產方獲得賠償,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為損害后果(吉蘭-巴雷綜合征)是由藥品所造成這一因果關系很難舉證,其二為該藥品獲得國家藥監部門批準,不屬于產品質量法中規定的“產品質量缺陷”,而產品質量缺陷是人身損害賠償的前提。
“從侵權責任法角度出發,如果損害后果(吉蘭-巴雷綜合征)是由藥品所造成這一因果關系能夠證明,那么受害者可以考慮從醫療機構對神經節苷脂這一藥品的用藥風險——如存在造成吉蘭-巴雷綜合征損害——沒有對患者進行告知,損害了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由此主張損害賠償責任。
在章李看來,讓患者承擔全部用藥風險明顯顯失公平,目前我國已經針對疫苗藥品不良反應建立的補償及賠償制度,呼吁國家從法律層面對其他藥品不良反應的補償或賠償制度也早日建立并完善起來。
對于不良反應補償問題,北京同仁京苑醫院馬森寶院長也提出通過建立保險機制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他說目前醫療意外風險保險主要是針對手術設立的,如果把藥品不良反應納入意外風險保險,可以減少當事人的損失,有利于化解一些矛盾,構建比較和諧的醫患關系。
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教研室副主任王岳認為,在沒有關于藥害賠償法規可供遵循的情況下,應該參考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盡快建立藥品不良反應補償救濟機制,設立“中國藥品不良反應研發和救濟基金”,以降低藥品不良反應各方無過錯當事人的經濟損失和風險。該基金的來源可以是三個方面:藥品生產商或進口商的藥品準備金或稱為風險基金;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助;社會捐助。(內文中患者均為化名,本人實習生陶凱倫亦有貢獻)
(編輯: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