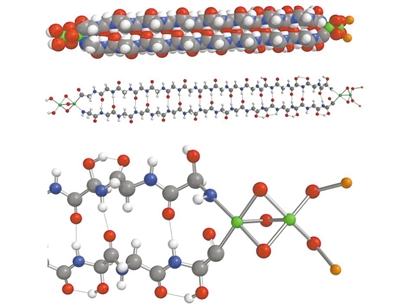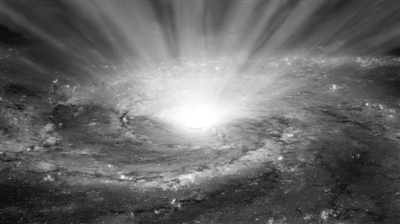當人類消失后,野生動物的生活會變成什么樣?
近日來,一群亞洲象“離家出走”的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持續關注,網友緊跟象群動態一路“追劇”,想看看它們最終會走到哪里。從“一路象北”的象群到闖入村莊的東北虎“完達山一號”,再到此前在上海100多個小區現身的貉、奔跑在武漢二環上的野豬,近兩年,野生動物頻頻“出圈”與人類不期而遇,讓人們再度思考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系。
不久前,一部由Apple TV+出品的紀錄片《地球改變之年》上線,同樣引發了廣泛的反響。它從另一個視角展現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人類消失后,野生動物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當封鎖持續1個月、3個月、6個月
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各國開始采取封鎖措施。疫情讓人類按下了暫停鍵,與此同時,自然界開始發生驚人的變化。從封鎖隔離起,《地球改變之年》的攝制組立即開始在五大洲進行拍攝,記錄這一次“史無前例的全球性實驗”。
首先顯現出來的變化,是世界變得安靜了。封鎖一開始,全球交通噪聲就減少了70%。在美國舊金山,交通噪聲降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此時,研究人員發現,金門大橋下的白冠麻雀求偶聲中出現了新的音調,這些鳥迎來多年來最好的繁殖季。
全球空氣污染的減輕速度也令人驚訝。在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印度,封鎖僅僅12天后,就出現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在霧霾后隱藏了30年的喜馬拉雅山,突然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年輕人對著鏡頭激動地說:“有生以來第一次晴空萬里,我們看到了喜馬拉雅山。”
“當人類暫停下來,地球得以再次呼吸。”講解人大衛·愛登堡在片中說道。
封鎖持續一個月后,曾經人滿為患的佛羅里達海灘空無一人,海龜開始回到曾經被人類占領的海灘安靜地產卵,生育率從40%提高到了61%。
在阿拉斯加海岸,游輪的減少使附近的海洋寧靜了25倍,海中的座頭鯨終于可以放心地去更遠的地方覓食,而不用擔心鯨魚寶寶聽不到自己的呼喚。往年,座頭鯨幼崽長到成年的幾率只有7%,2020年,無疑會有更多的幼鯨生存下來。
封鎖進行了3個月,城市人流量大幅減少,動物們開始享受城市生活。在南非,一只河馬悠閑地散步到加油站;在以色列,胡狼們在公園里曬太陽;在智利,美洲豹跑上了人行道。
那些平日里靠人類存活的動物,是否會因此挨餓呢?在日本奈良,寺廟前的梅花鹿一直以游客喂食為生,當人類消失,它們循著記憶穿過城市道路,找到了曾經覓食的草地,吃到了原本屬于它們的食物——青草和樹葉,這些食物讓它們更健康。
封鎖進行了6個月,大自然的復興仍在繼續。印度恒河的含氧量增加了80%,摩洛哥的海水清潔度評級從差躍升到優良。
在南非開普敦的海邊,非洲公驢企鵝的幼崽告別了餓肚子的生活。往常,這些企鵝父母每天早上出海捕魚,但回家路上那擠滿游客的海灘讓它們望而卻步,它們只好等夕陽西下、游客散去,才踏上回家的路,因此企鵝寶寶一天只能吃一頓飯。現在,企鵝父母一天可以來回兩三次,小家伙們的伙食量大大提高。
當封鎖持續一年,世界已經發生了驚人的改變,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超過6%,降幅是歷史之最。隨著旅行和工業造成的震動減少一半,這一年也成為有史以來地下最安靜的時間。
“封鎖不會永遠持續,但它讓我們從中得到啟迪。”講解人大衛·愛登堡在片中說。
在保護與發展中尋找平衡
“這部紀錄片總體上拍攝得很真實,視角也很獨特,里面很多地方我都去過,觀看時覺得很熟悉。”中國林業科學院森林生態環境保護研究所研究員李迪強說。
在李迪強看來,人類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往往是通過對它們生境的影響造成的。對于從事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多年的他來說,這種情況屢屢得見。比如,近些年來他持續追蹤調查的野駱駝,就因人類活動受到很大影響。
野駱駝曾在100年前被認為早已消亡,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于庫姆塔格沙漠發現蹤跡,成為世界駱駝科唯一幸存的野生物種。2007年,李迪強擔任科技部“庫姆塔格沙漠綜合科學考察”項目動物調查組組長,開始利用紅外相機、分子糞便學和GPS頸圈等手段,對野駱駝的分布和數量、種群與行為生態學、遷移規律和遺傳學等進行追蹤調查。
在野駱駝分布區,李迪強曾經看到遍地的修路、探礦、采礦等人為痕跡,這些人為痕跡會侵占野駱駝的水源點,而水源點一旦被破壞,周圍十幾平方公里的生境就不得不被野駱駝放棄,導致其生存受到嚴重影響。同時,修路也使野駱駝種群分布區的完整性遭到進一步破壞,為野駱駝的繁衍增加難題。
“一旦人類活動減少,包括野駱駝在內的野生動物就又慢慢回來了,這是我們最近去看到的情況。”李迪強說。
除了通過對生境的破壞影響野生動物生存外,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孫全輝看到的還有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更直接的影響。
“比如,在一些東南亞國家旅游景點盛行的騎乘大象項目,就對大象生存狀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也刺激了對大象的盜獵和抓捕。”孫全輝說。
“在人類和野生動物的關系中,保護與發展的矛盾是沖突的核心主題。”李迪強說,比如,在東北虎豹國家公園,老百姓會放置獵套套住野生動物,因為他們的耕地被國家公園的林地包圍,野豬等野生動物就會去吃他們的莊稼、牲畜。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不停地剪套子,老百姓就不停地下套子。“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控制套子就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東北虎豹國家公園鼓勵當地人們發展替代經濟,比如種蘑菇、木耳或者養蜂,來增加經濟收入,試圖在保護與發展中尋找平衡。”孫全輝說,“這些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這些年東北虎逐漸從邊境地區開始向內陸擴散,出現在之前已經沒有蹤跡的一些地方。當它們來到人類的居住區,又帶來了人獸沖突的新問題,比如之前闖入村莊的‘完達山一號’。對人類與野生動物如何和諧共處,研究與探索遠未結束。”
尊重與共生
在紀錄片《地球改變之年》的彈幕和評論區里,兩種聲音在“打架”,一種觀點認為“人類才是地球的毒瘤、癌癥”,另一種則反駁說“沒有人類,一些物種也會滅絕,人類也要發展”。
“這兩種極端的看法當然都是不可取的。”孫全輝說,“首先我們不能反人類,任何解決的方式都要從人的角度出發,但同時,要想緩解人與野生動物的沖突,關鍵也在于人,動物不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只能從自身入手。最重要的是找到人與野生動物安全的邊界。”
在李迪強看來,每個物種都有其生存的智慧,它們在幾百萬年甚至更長時間與環境打交道并生存下來的過程里,積累了豐富的基因信息,這是我們認識自然的一把鑰匙。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應該促進所有物種和諧共存。拯救瀕危物種,也是生物多樣性最核心的話題。同時,從人類自身發展來說,我們的高質量生活也必然需要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狀態。
《地球改變之年》的結尾就講述了一個人類與野生動物化敵為友的故事。在印度一個偏僻小山村里,村民和大象有著時間久遠且無法調和的矛盾。
村民為了生存不斷開拓田地,導致大象的自然棲息地僅剩5%,而大象為了生存不得不破壞田間植物,人象矛盾由此產生。每年,人與大象的沖突造成各自死傷無數。
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外出務工人員回到了家里。自然保護組織開始聯合這些空閑的勞工,在村莊和森林之間制造了一片緩沖地帶,用來種植速生水稻和草給大象食用。
村民虔誠地祈禱,大象有了食物之后就不再毀壞農田、進入村莊。而事實確實如他們所愿,大象在村外吃完緩沖帶的植物之后就離開了。
當印度的村民找到與大象更好的相處模式時,科學家們也在思考,是否可以通過減少游輪交通、每年特定時期夜晚關閉海灘來與野生動物達到和諧共生。
而在此次云南“一路象北”的過程中,當地也采取了多種措施保障人象安全,消防人員持續用無人機對象群實施勘察、跟蹤,沿途有應急人員為象群設置香蕉、玉米、菠蘿等食物的投食區避免其破壞農作物,設置誘導道路引導象群遠離人群、進入人煙稀少的林區,等等。
在孫全輝看來,此次的亞洲象北遷既是野生動物保護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也是重構公眾對人與野生動物關系認知的絕佳機會。如果說以前的人們對人獸關系的認知還停留在恐懼和制伏,那么現在人們更愿意看到人與野生動物的尊重與共生。“北遷的大象最終會落腳何處現在還未知曉,但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關系的發展方向一定會是彼此尊重、和諧共生。”